28-07-20
下半生,想做懶鶴,東住住,西躺躺。
除了香港,最熟悉的城市是台北——朋友在那裏,法律業務曾在那裏,我的故事留在那裏。忽離忽別,誤華年。
台北,億萬年前,是內陸湖的盤底,由於地理優勢,成為台灣的經濟中心,不計算周邊,台北市只有兩百多萬人口。台北的文化是談生活、談人;香港的文化是談機會、談錢。十七世紀,西班牙人在淡水海邊「落腳」,建「聖多明哥城」(Fort San Domingo),後被荷蘭人趕走。1895至1945年,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,那些老房子,像淺草。
香港有7-Eleven,台北有我心愛的Family Mart。對於可憐現代人,便利店是家,每晚回酒店前,在Family Mart尋寶,地方大得可以在店內盛宴,買了一碗關東煮、一盤芭樂、一杯熱牛奶,靜坐,望著玻璃外,一對戀人要分手,台北的冬雨,慣說別離言,哀無邊。
1979年,我第一次擁抱鐵鳥的翅膀,異地是台北,只因為機票便宜。當時,台北比香港落後,樓宇殘舊,路上滿是汽油味;最萌是老太婆,受日本影響,愛穿花裙、塗上口紅,見人會鞠躬。繁榮地方只有西門町,如旺角般,多路邊攤。問永安大飯店的接待:「Shopping在哪裏?」答:「鐵路後面的中華商場。」(那時的西門町,有一條大鐵路)天呀,原來像香港中環街市的「物體」;那年代東區還有農田,更不用說「台北101」的「潮人」信義區,而賣「來佬時裝」的中興百貨,八十年代才開業,只是香港永安百貨的簡化版,在2008年,中興不敵新型商場,關燈告別。
七十年代,香港年輕人放洋的不多,考不上本地大學,家裏又沒有錢的,便去台灣唸大學,香港人被叫「僑生」,學費免收,還有津貼。那邊的同學帶我去「夜店」,客人穿短褲、涼鞋,喝的是台灣啤酒,吃的是花生,紅男綠女腳踏花生殼,跳cha-cha-cha,小舞池填滿人頭的波浪,青春無悔,大唱劉文正的《舞在今宵》:「dancing all night,請別把我忘懷……」讓我想起當今「五月天」的《傷心的人別聽慢歌》,台北總和我餘情未了。
昔日,台北難忘的是兩件事:晚上戒嚴和電單車(他們叫「機車」)。在七、八十年代,台北的經濟發展受制於1949年頒佈的戒嚴令(curfew),持續三十八年,在1987年宣佈結束:晚上,我們在中山北路一帶,約11時吧,聽到街頭的警報聲,便要「雞飛狗走」,慌忙地趕回飯店,計程車都給搶光,只好坐上像今天曼谷的「白牌電單車」,在極速公路上,尷尬地緊抱司機的肥腰,這是最不情願的性騷擾。
四十年來,為公為私,一年總會跑台北數次,許多地方,比台北人還要熟悉:有些館子,老闆都仙遊;我來往的律師事務所,合夥人更替了三代;懷舊的「紅包場」(老歌廳,歌星穿著廉價的華麗晚禮服,唱六、七十年代的金曲,觀眾為了獎勵偶像,送上紅包打賞)和「民歌餐廳」(流行於八、九十年代,歌手多是年輕讀書人,拿著木結他自彈自唱,巨星如周華健、張宇也曾駐場)全部關門;「外省人」(1949年前後,因內戰由大陸遷居台灣的移民,他們來自湖北、江蘇、山東等地)主導的生活方式亦日漸式微;我還記得當年的電視台,不准用台語廣播,要用「國語」。不過,九十年代開始,台灣改革開放了,台北的物質水平,一天比一天進步,而且台北的美麗,到了今天還是獨特的:生活空間和文化。
生活,不是早上起來,上班、抓吃、看手機、睡覺,這般簡單,這只是人肉機器的流程。生活,是一種「人的文化」,它是什麼?台灣作家龍應台解釋:「文化體驗在一個人如何對待他人、對待自己、對待所處的自然環境。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沉的社會裏,人懂得尊重自己——他不苟且,所以有品味;人懂得尊重別人——他不霸道,所以有道德;人懂得尊重自然——他不掠奪,所以有永續的智慧。有文化的人,一顰一笑 、整體氣質,都不一樣;一隻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,他是憐憫地避開,還是一腳踢過去?電梯門打開,他是謙抑地讓人,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?」
台北有文化底氣,當然是相對的說法。在七、八十年代,謀生困難,教育未普及,這城市也有粗魯的基層,萬華區的華西街,一樣擠滿黑道和娼館,我經過艋舺,「地膽」的眼神如利刀;而在今天,我再感受不到台北的年輕人有著從前的溫柔。
台北人重視教養,有她的歷史原因(台灣東南部的城市,和台北是不同的世界):在戰後,從大陸去台灣的「外省人」,前前後後,有過百萬人,當然,戰後來香港移民的人數也不少,但許多只是農民。相反,從1949年開始,蔣介石籌備撤軍退守台灣,他認為台灣的發展建設,要靠才俊,於是把社會各階層的精英如教授、新聞、科研、文人等人才,帶到台灣,多定居台北。我們唸書的六、七十年代,許多中外書籍,便是台灣出口的;動人的電影如《養鴨人家》、《冬暖》、《秋決》等,亦是台灣過來的;精緻的好歌,如《今天不回家》、《往事只能回味》、《橄欖樹》等,皆由台灣外輸。聽說在九十年代末,台灣的書店多達四千家,敦化南路24小時的「誠品書店」九十年代才出現,我躲進去,夜未央。之前,我們擠往「金石堂書店」打書釘,瓊瑤的小說,一定買幾本回香港。她寫初戀的作品《窗外》,是十九歲林青霞的首演,一炮而紅;林青霞是港男對台灣女生的幻想,有氣質、有教養。
三十年代,日本人在衡陽路一帶,經營咖啡店。台北的咖啡店,歷史悠久,一向是讀書人出沒的地方。八十年代,咖啡店叫做「舊情綿綿」,文雅浪漫到死。九十年代,我最愛忠孝東路四段的Tu cafe,漂亮的文青在那裏談及幸福,我在那裏渡過無數晚上。台北的茶店如恆河沙數,花草樹木都可以變成茶。生活的「小確幸」,在台北輕易找到,因為台北人珍惜家庭和工作間以外的第三個地方,也是社會學家所說的「第三空間」(third place)概念。「第三空間」在大城市中,讓人們得以逃離繁瑣日常,像心靈躲避所。在香港,走進任何一家Starbucks或Pacific Coffee,人們都是談工作;在台北,咖啡室卻是發獃自療的好地方,因為在台北,生活的空間大很多,台灣近年發展近機場的林口和近淡水河的新北,漂亮時髦。在台北,屁股樂於尋覓一處方位憩息,看著小鳥啄食地上的陽光;或跑去綠得過分的民生社區,在老房子門前,找間雪糕店。「年與時馳」,年輕人要把握光陰,做啄食的小鳥,而不是觀鳥的閒人?
問台北的朋友:「在台北買房子好嗎?」他說:「這二十多年來,台灣的經濟一般,我們的人口,只有二千多萬,外來人不多,租金回報非常低。台北不是香港,光是『炒樓』和『炒股票』,活不下去。聽說香港有些人,想移居台北,追求心目中的『小確幸』。如果從經濟上考量,這不是一個好主意:台北並非一個國際中心,工種不多,而新科技行頭,又不是香港人的專長。想搞點零售生意,但是,台灣不崇尚消費主義,夢想來當一個文青,文化根底未必夠厚;還要學懂台語呢。台北賺港幣一萬元月薪的人,比比皆是,扣除生活開支後,還剩多少錢寄回香港的爸媽?」
台北適宜一些「家有恆產」,不用擔心生計的人家,一年停留三個月,享受異地生活「staycation」的樂趣,那叫「居遊」,在這充滿文化和空間的城市,宿遊旅居。朋友被派去台北工作,我問:「生活如何 ?」他笑笑:「比對香港,台北是『寧靜』的!」我說:「早猜到你這麼說。」他點頭:「香港人太氣盛,忙於安排今天、明年、下輩子的事情,操心的都是收入和物質。台北人,注重家庭生活樂趣,晚上,回家吃飯的人多,在外面流連的人少,館子過了十時,『歐巴桑』已收拾地方。老百姓追求安穩的生活,一年買多少套新衣、去多少次旅行不重要,要別人加班,加工錢也未必答應;你興高采烈提出做生意的大計,他們聽過後,轉身便把念頭打消。」
台北人的「easy」態度,有三個原因。台灣是一個島,島,可以獨善其身,不必和很多國家擦邊;在台北,新聞消息都不用國際化,你看,消防員拯救一隻小貓,都可以是電視新聞。第二,在台北,平常百姓佔多數,沒有香港那「鑽石和塑膠粒」的平行貧富差距。加上生活費用不高,人們祥和。最後,因歷史的關係,台灣定於某種空間,人們慣於風浪,隨變而活。
從香港人的標準,我發覺台北人的「隨和」有時候變得「隨便」,因為他們是「人尊」的社會,和香港「法尊」的社會不一樣:兩個台北人在吵架,可能以道德為依據;兩個香港人在爭執,必然根據法例在舌劍。這些事情,對於我作為一個律師,感受特別深。有一次,對一個台灣客戶在法律上說不,她的反應是:「你沒有人情味,不把我看作朋友!」另一個例子,香港的公共泳池管理,一絲不苟,到處都是警告牌,嗅到的是漂白水味道;台北的泳池「人氣」十足,守門口的,像個鄰居,招待處擺放私人東西,完全是家庭式。近十年,香港變了,非常冰冷,有什麼事情,想找人查問,飽受欺凌:答案往往是「你上網查、手機apps……」。假如香港不以文化和修養去改善社會,繼續以金錢掛帥,就算更高的GDP,只會衍生更可怕的惡行。
想一年在台北staycation數月,另外一個考慮是地震,台北人習慣了地震,香港人卻怕得要死。有一次,我住的酒店,震得很厲害,遊客跑到地面避難,抱在一團,以為是世界末日。當然,位於地震帶,「好處」是有溫泉,台北的山邊有著大大小小的溫泉,開車去到如夢境的烏來,望著河,輕煙在飄,思念舊時人。
想在香港以外,建立多一個亞洲驛居,到底在哪?我仍在掙扎:東京的浮華?青島的海韻?曼谷的熱艷?還是台北的樸樂?
下一站,在寂寞的街燈下,雨朦朧,誰又等候與你共舞?
此網誌也上載於下列網站: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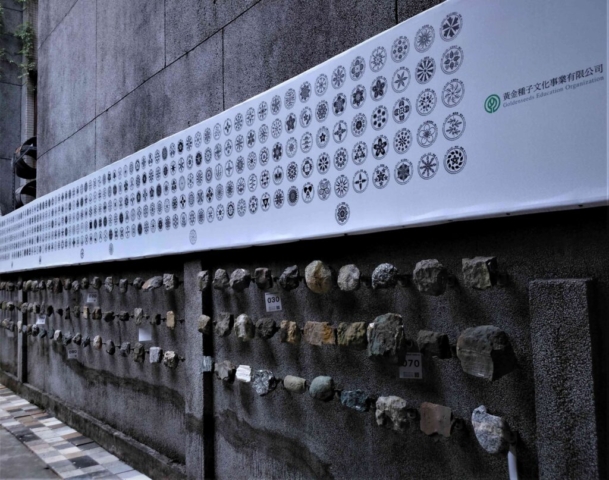

-copyrighted-by-張哲生-640x480.jpg)




